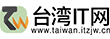小浪底小姑奶奶的风雨沟
 (资料图片)
(资料图片)
又是一年风吹麦浪,又是一年杏儿飘香,时光的脚步,匆匆,太匆匆……
周末出行,田野里,大片变黄的麦田,风吹过,泛起一波又一波金色的麦浪,感觉亲切的无以言表,而那些一掠而过的杏树们,带着一树亮灿灿的红黄,连同那明媚的阳光,在我的心里绽放出香甜的芬芳……
滔滔东流的黄河水,因了小浪底水库的建设,褪去了深黄,披上了绿装,清新清澈。只有那留存在脑海深处的记忆,一直静静地、原汁原味地在岁月的长河里流淌着,一如我生命中那些最珍贵的标签,完好无缺,依然还是旧时模样。
那个位于黄河北岸,那个叫做风雨沟的小山村,带着质朴、带着热情、带着甜蜜,扑面而来。
小时候,我住在黄河南岸的小浪底村,黄河北岸正对外婆家的一条小山沟,叫做风雨沟,隶属济源大峪,沟里仅仅生活着四户人家,可能有十几口人吧。
沟底有一条清溪潺潺流出,汇入到黄河里。这条小溪将沟里生活的四户人家分开,两户在沟西,两户在沟东。
沟西上方一家就是我的小姑奶奶(母亲的小姑)家。下方的两孔窑洞里生活着一对中年夫妻,妻子精神不正常,白天一直坐在门口自言自语地唠叨着自己才听得懂的话。
沟东生活着两家人,其中一家是耿叔家。耿叔是父亲水文站的同事,他有5个孩子,是风雨沟人口最多的人家。东沟的另一家我不知道是谁,只知道还有一家人,但从来没见过,也不知道家里有几口人。
风雨沟与小浪底一河之隔,非汛期的时候,站在对岸喊叫,就可以听见。不过风雨沟的人要到沟口,小浪底的人要到黄河岸边才可以。
从我记事开始,每年都要去风雨沟无数次,首先是逢年过节要去姑奶奶家走亲戚,每次去按节日不同而带不同的礼物,比如八月十五送糕(一种大大的发面枣糕);其次是从初夏到秋季瓜果桃杏成熟的时候,那是有空就过黄河到姑奶奶家去,目的明确,目标精准,动力十足。
农历五月,正是麦黄杏成熟的时候。
在我们小浪底村,由于人口众多,儿童当然也多,很少有桃杏长到成熟的机会,早在青涩酸楚的时候就被洗劫一空,只有人口稀少的风雨沟里,那些果子能完整地生长到成熟。
于是,每当这个时候,我和弟弟们便会一次次地渡过黄河,提着篮子来到风雨沟,在果树上尽情地施展拳脚,大快朵颐,走的时候,还要把篮子装满。
姑奶奶家后山半山腰,有一棵枝繁叶茂果实累累的大杏树,因为这里人少而得以保存完整。每次我们去,提着篮子爬上树一个个地摘杏,一边摘一边吃,很快也能摘满篮子。有时候姑奶奶会给我们一根竹竿,让我们对着杏树一阵敲打,落下一地的黄杏和绿叶来,一个个捡起,很快就满满一篮了。
风雨沟东沟耿叔家有五个孩子,他儿子黄河、双河跟我和弟弟年龄相当,他们怎么不来摘这些杏呢?有两个原因,一是东沟西沟之间的沟太深,他们不能直接过来,而要跑到黄河边的沟口才能下到沟底,再走一公里才能到杏树下;二是他们自己家的果树非常多,应有尽有,根本不稀罕西沟这边的果树。
对我来说,最最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到东沟去看过,只是隔沟向东张望,鸡犬之声相闻,窑洞房屋俨然,树木繁茂,偶尔看见耿叔家的小孩露头。
姑奶奶家院子外有一棵梨树,院子里有几棵石榴树,还有一棵遮住半个院子的葡萄架,这些树都在我和弟弟贪婪的目光中一天天地变化着,直到果实成熟。
有时候姑奶奶会捎口信给我们,说某果实熟了,可以来摘了。但多数时候我们这支摘果小分队,都是提前到达,先试吃几次,直到成熟的时候,再一扫而空。
而且每次去的时候,都能得到姑奶奶好吃好喝的招待,这就更助长了我们的采摘气焰。
长大成人后,我再也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麦黄杏儿了。
前几日回父母家,看到母亲买的杏儿,黄黄的也很好看,便拿了一个洗洗,满怀期望地送入口中,仅仅是咬了一口,那酸爽简直要了我的命。
皱眉吐舌放下酸杏,跟母亲说起当年去姑奶奶家摘的麦黄杏,说到姑奶奶家门外的那棵梨树,院子里的石榴树和葡萄树。
母亲轻轻摇着满头的白发,慢悠悠地说:风雨沟没有了,姑奶奶走了,那些好吃的果子就更没有了。
小浪底水库的修建,将风雨沟沉入碧水清波之中,每每回到小浪底,看到高高的小浪底大坝,就会想到大坝北端下的风雨沟,想到那条深深的长长的沟,想到那条清溪,想到我一直想深入探险而未能走进的小溪上游,想到那满沟飘香的果树,想到白白净净高高瘦瘦的姑奶奶,还有很多很多,只是他们再也不能走进我的视线,只能在我的记忆里温柔地存在着,不会走远。
风吹麦浪,杏儿飘香。
在这收获与播种、杏儿飘香的季节,尽管我没有品尝到美味的甜杏儿,但我依然感受到了幸福与快乐,因为我有美丽的风雨沟,有温暖的过往,有浓浓的亲情,还有依然存在的感动……
(本文写于2020年)
(图片来自网络,侵权联系删除)作者简介:相茹,河南作家协会会员,郑州作家协会会员。居郑州,爱旅行爱写作,爱一切美好的人和事。
关键词: